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西屯評價與財務模組會計服務推薦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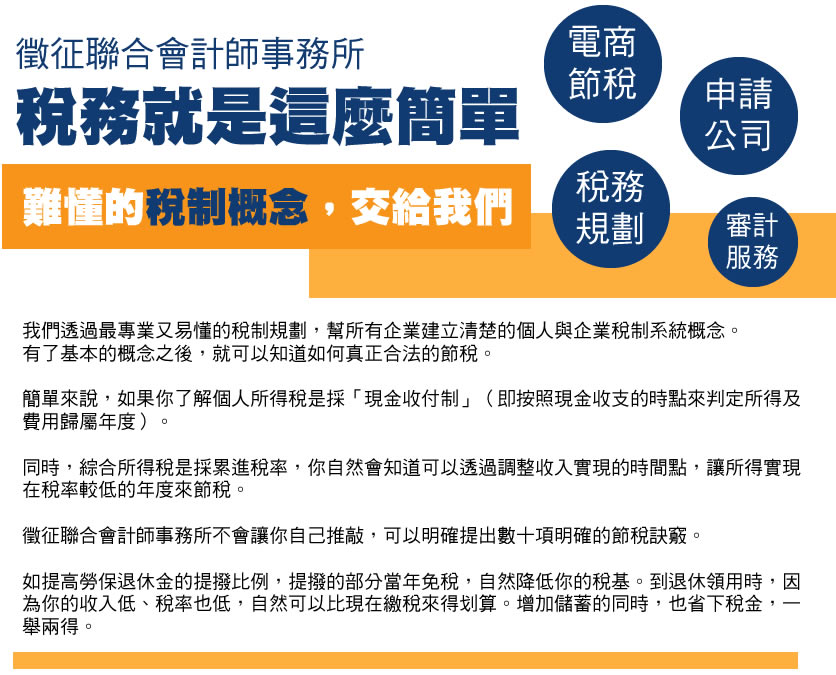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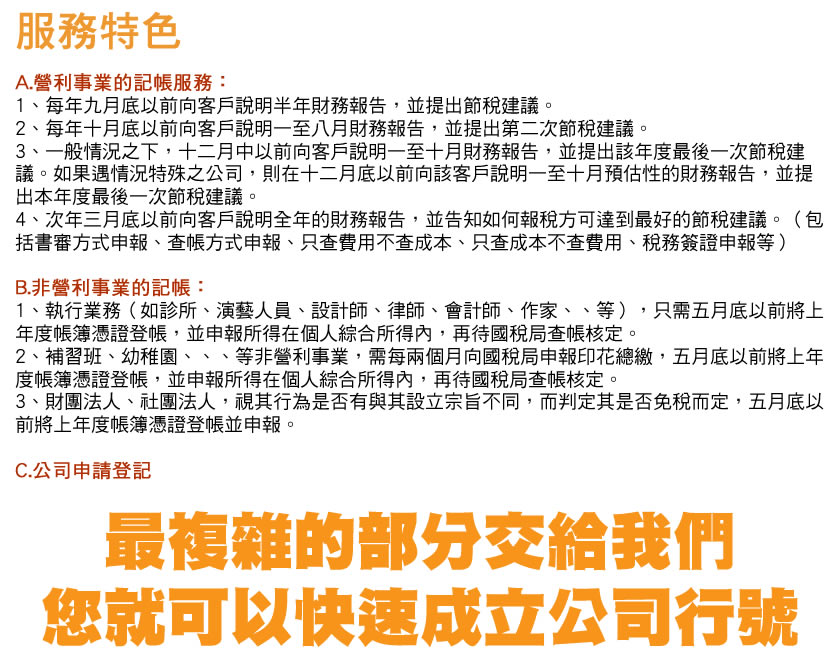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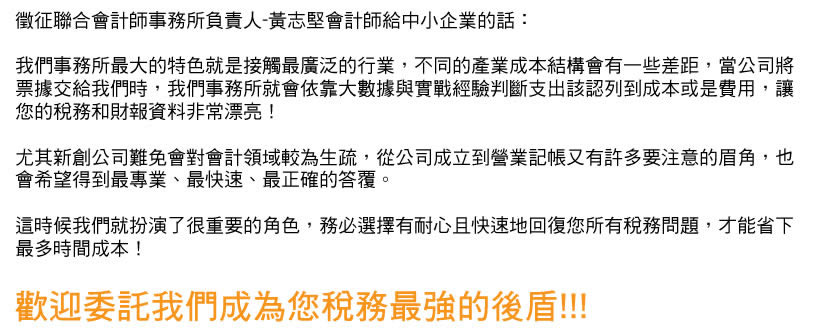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北區移民顧問會計服務推薦, 台中大里稅務管理與諮詢, 台中推薦會計稅務會計服務推薦
老舍:兔 一 許多人說小陳是個“兔子”。 我認識他,從他還沒作票友的時候我就認識他。他很瘦弱,很聰明,很要強,很年輕,眉眼并不怎么特別的秀氣,不過臉上還白凈。我和他在一家公司里共過半年多的事,公司里并沒有一個人對他有什么不敬的態度與舉動;反之,大家都拿他當個小兄弟似的看待:他愛紅臉,大家也就分外的對他客氣。他不能,絕對不能,是個“兔子”。 他真聰明。有一次,公司辦紀念會,要有幾項“游藝”,由全體職員瞎湊,好不好的只為湊個熱鬧。小陳紅著臉說,他可以演戲,雖然沒有學過,可是看見過;假若大家愿意,他可以試試。看過戲就可以演戲,沒人相信。可是既為湊熱鬧,大家當然不便十分的認真,教他玩玩吧,唱好唱壞有什么關系呢。他唱了一出《紅鸞喜》。他的嗓子就和根毛兒似的那么細,坐在最前面的人們也聽不見一個字,可是他的扮相,台步,作派,身段,沒有一處不好的,就好象是個嗓子已倒而專憑作工見長的老伶,處處細膩老到。他可是并沒學過戲!無論怎么說吧,那天的“游藝”數著這出《紅鸞喜》最“紅”,而且掌聲與好兒都是小陳一個人得的。下了裝以后,他很靦腆的,低著頭說:“還會打花鼓呢,也并沒有學過。”不久,我離開了那個公司。可是,還時常和小陳見面。那出《紅鸞喜》的成功,引起他學戲的興趣。他拜了俞先生為師。俞先生是個老票友,也是我的朋友;五十多歲了,可是嗓子還很嬌嫩,高興的時候還能把胡子剃去,票出《三堂會審》。俞先生為人正直規矩,一點票友們的惡習也沒有。看著老先生撅著胡子嘴細聲細氣的唱,小陳紅著臉用毛兒似的小嗓隨著學,我覺得非常有趣,所以有時候我也跟著學幾句。我的嗓子比小陳的好的多,可就是唱不出味兒來,唱著唱著我自己就笑了,老先生笑得更厲害:“算了吧,你聽我徒弟唱吧!”小陳微微一笑,臉向著墻“喊”了幾句,聲音還是不大,可是好聽。“你等著,”老先生得意的對我說,“再有半年,他的嗓子就能出來!真有味!” 俞先生拿小陳真當個徒弟對待,我呢也看他是個小朋友,除了學戲以外,我們也常一塊兒去吃個小館,或逛逛公園。我們兩個年紀較大的到處規規矩矩,小陳呢自然也很正經,連句錯話也不敢說。就連這么著,俞先生還時常的說:“這不過是個玩藝,可別誤了正事!” 二 小陳,因為聰明,貪快貪多,恨不能一個星期就學完一出戲。俞先生可是不忙。他知道小陳聰明,但是不愿意教他貪多嚼不爛。俞先生念字的正確,吐音的清楚,是票友里很少見的。他楞可少教小陳學幾個腔兒,而必須把每個字念清楚圓滿了。小陳,和別的年輕人一樣,喜歡花哨。有時候,他從留音機片上學下個新腔,故意的向老先生顯勝。老先生雖然不說什么,可是心中不大歡喜。經過這么幾次,老先生可就背地里對我說了:“我看哪,大概這個徒弟要教不長久。自然嘍,我并不要他什么,教不教都沒多大關系。我怕的是,他學壞了,戲學壞了倒還是小事,品行,品行……不放心!我是真愛這個小人兒,太聰明!聰明人可容易上當!” 我沒回答出什么來,因為我以為這一半由于老先生的愛護小陳,一半由于老先生的厭惡新腔。其實呢,我想,左不是玩玩吧咧,何必一定叫真兒分什么新舊邪正呢。我知道我頂好是不說什么,省得教老先生生氣。 不久,我就微微的覺到,老先生的話并非過慮。我在街上看見了小陳同著票友兒們一塊走。這種票友和俞先生完全不同:俞先生是個規規矩矩的好人,除了會唱幾句,并沒有什么與常人不同的地方。這些票友,恰相反,除了作票友之外,他們什么也不是。他們雖然不是職業的伶人,可也頭上剃著月亮門,穿張打扮,說話行事,全象戲子,即使未必會一整出戲,可是習氣十足,我把這個告訴給俞先生了,俞先生半天沒說出話來。 過了兩天,我又去看俞先生,小陳也在那里呢。一看師徒的神氣,我就知道他們犯了擰兒。我剛坐下,俞先生指著小陳的鞋,對我說:“你看看,這是男人該穿的鞋嗎?葡萄灰的,軟梆軟底!他要是登台彩排,穿上花鞋,逢場作戲,我決不說什么。平日也穿著這樣的鞋,滿街去走,成什么樣兒呢?” 我很不易開口。想了會兒,我笑著說,“在蘇州和上海的鞋店里,時常看到顏色很鮮明,樣式很輕巧的男鞋;不比咱們這兒老是一色兒黑,又大又笨。”原想這么一說,老先生若是把氣收一收,而小陳也不再穿那雙鞋,事兒豈不就輕輕的揭過去了么。 可是,俞先生一個心眼,還往下釘:“事情還不這么簡單,這雙鞋是人家送給他的。你知道,我玩票二十多年了,票友兒們的那些花樣都瞞不了我。今天他送雙鞋,明天你送條手絹,自要伸手一接,他們便吐著舌頭笑,把天好的人也說成一個小錢不值。你既是愛唱著玩,有我教給你還不夠,何必跟那些狐朋狗友打聯聯呢?!何必弄得好說不好聽的呢?!” 小陳的臉白起來,我看出他是動了氣。可是我還沒想到他會這么暴烈,楞了會兒,他說出很不好聽的來了:“你的玩藝都太老了。我有工夫還去學點新的呢!”說完,他的臉忽然紅了;仿佛是為省得把那點靦腆勁兒恢復過來,低著頭,抓起來帽子,走出去,并沒向俞老師彎彎腰。 看著他的后影,俞先生的嘴唇顫著,“嘔”了兩聲。“年輕火氣盛,不必——”我安慰著俞先生。 “哼,他得毀在他們手里!他們會告訴他,我的玩藝老了,他們會給他介紹先生,他們會躥弄他‘下海’,他們會死吃他一口,他們會把他鼓逗死。可惜!可惜!” 俞先生氣得不舒服了好幾天。 三 小陳用不著再到俞先生那里去,他已有了許多朋友。他開始在春芳閣茶樓清唱,春芳閣每天下午有“過排”,他可是在星期日才能去露一出。因為俞先生,我也認識幾位票友,所以星期日下午若有工夫,我也到那里去泡壺茶,聽三兩出戲;前后都有熟人,我可以隨便的串——好觀察小陳的行動。就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人說他是“兔子”。我不能相信。不錯,他的臉白凈,他唱“小嗓”;可是我也知道他聰明,有職業,靦腆;不論他怎么變,決不會變成個“那個”。我有這個信心,所以我一邊去觀察他的行動,也一邊很留神去看那些說他是“那個”的那些人們。 小陳的服裝確是越來越匪氣了,臉上似乎也擦著點粉。可是他的神氣還是在靦腆之中帶著一股正氣。一看那些給他造謠的,和捧他的,我就明白過來:他打扮,他擦粉,正和他穿那雙葡萄灰色的鞋一樣,都并不出于他的本心,而是上了他們的套兒。俞先生的話說得不錯,他要毀在他們手里。 最惹我注意的,是個黑臉大漢。頭上剃著月亮門,眼皮里外都是黑的,他永遠穿著極長極瘦綢子衣服,領子總有半尺來高。 據說,他會唱花臉,可是我沒聽他唱過一句。他的嘴里并不象一般的票友那樣老哼唧著戲詞兒,而是念著鑼鼓點兒,嘴里念著,手腳隨著輕輕的抬落;不用說,他的工夫已超過研究耍腔念字,而到了能背整出的家伙點的程度,大概他已會打“單皮”。 這個黑漢老跟著小陳,就好象老鴇子跟著妓女那么寸步不離。小陳的“戲碼”,我在后台看見,永遠是由他給排。排在第幾出,和唱哪一出,他都有主張與說法。他知道小陳的嗓子今天不得力,所以得唱出歇工兒戲;他知道小陳剛排熟了《得意緣》,所以必定得過一過。要是湊不上角兒的話,他可以臨時去約。趕到小陳該露了,他得拉著小陳的手,告訴他在哪兒叫好,在哪兒偷油,要是半路嗓子不得力便應在哪個關節“碼前”或“叫散”了。在必要的時候,他還遞給小陳一粒華達丸。拿他和體育教員比一比,我管保說,在球隊下場比賽的時候那種種囑告與指導,實在遠不及黑漢的熱心與周到。 等到小陳唱完,他永遠不批評,而一個勁兒夸獎。在夸獎的言詞中,他順手兒把當時最有名的旦角加以極厲害的攻擊:誰誰的嗓子象個“黑頭”,而腆著臉硬唱青衣!誰誰的下巴有一尺多長,脊背象黃牛那么寬,而還要唱花旦!這種攻擊既顯出他的內行,有眼力,同時教小陳曉得自己不但可以和那些名伶相比,而且實在自己有超過他們的地方了。因此,他有時候,我看出來,似乎很難為情,設法不教黑漢拉著他的手把他送到台上去,可是他也不敢得罪他;他似乎看出一些希望來,將來他也能變成個名伶;這點希望的實現都得仗著黑漢。黑漢設若不教他和誰說話,他就不敢違抗,黑漢要是教他擦粉,他就不敢不擦。 我看,有這么個黑漢老在小陳身旁,大概就沒法避免“兔子”這個稱呼吧? 小陳一定知道這個。同時,他也知道能變成個職業的伶人是多么好的希望。自己聰明,“說”一遍就會;再搭上嗓子可以對付,扮相身段非常的好!資格都有了,只要自己肯,便能伸手拿幾千的包銀,干什么不往這條路上走呢!什么再比這個更現成更有出息呢? 要走這條路,黑漢是個寶貝。在黑漢的口中,不但極到家的講究戲,他也談怎樣為朋友家辦堂會戲,怎樣約角,怎樣派份兒,怎樣賃衣箱。職業的,玩票的,“使黑杵的”,全得聽他的調動。他可以把誰捧起來,也可以把誰摔下去;他不但懂戲,他也懂“事”。小陳沒法不聽他的話,沒法不和他親近。假若小陳愿意的話,他可以不許黑漢拉他的手,可是也就不要再到票房去了。不要說他還有那個希望,就是純粹為玩玩也不能得罪黑漢,黑漢一句話便能教小陳沒地方去過戲癮,先不用說別的了。 四 有黑漢在小陳身后,票房的人們都不敢說什么,他們對小陳都敬而遠之。給小陳打鼓的決不敢加個“花鍵子”;給小陳拉胡琴的決不敢耍壞,暗暗長一點弦兒;給小陳配戲的決不敢弄句新“搭口”把他繞住,也不敢放膽的賣力氣叫好而把小陳壓下去。他們的眼睛看著黑漢而故意向小陳賣好,象眾星捧月似的。他們絕不會佩服小陳——票友是不會佩服人的——可是無疑的都怕黑漢。 假如這些人不敢出聲,台底下的人可會替他們說話;黑漢還不敢干涉聽戲的人說什么。 聽戲的人可以分作兩類:一類是到星期六或星期日偶爾來泡壺茶解解悶,花錢不多而頗可以過過戲癮。這一類人無所謂,高興呢喊聲好,不高興呢就一聲不出或走出去。另一類人是冬夏常青,老長在春芳閣的。他們都多知多懂。有的玩過票而因某種原因不能再登台,所以天天上茶樓來聽別人唱,專為給別人叫“倒好”,以表示自己是老行家。有的是會三句五句的,還沒資格登台,所以天天來燻一燻,服裝打扮已完全和戲子一樣了,就是一時還不能登台表演,而十分相信假若一旦登台必會開門紅的。有的是票友們的親戚或朋友,天天來給捧場,不十分懂得戲,可是很會喊好鼓掌。有的是專為來喝茶,不過日久天長便和這些人打成一氣,而也自居為行家。這類人見小陳出來就嘀咕,說他是“兔子”。 只要小陳一出來,這群人就嘀咕。他們不能挨著家兒去告訴那些生茶座兒:他是“兔子”。可是他們的嘀咕已夠使大家明白過來的了。大家越因好奇而想向他們打聽一下,他們便越嘀咕得緊切,把大家的耳朵都吸過來一些;然后,他們忽然停止住嘀咕,而相視微笑,大家的耳朵只好慢慢的收回去,他們非常的得意。假若黑漢能支配台上,這群人能左右台下,兩道相逆的水溜,好象是,沖激那個瘦弱的小陳。這群人里有很年輕的,也有五六十歲的。雖然年紀不同,可一律擦用雪花膏與香粉,壽數越高的越把粉擦得厚。他們之中有貧也有富,不拘貧富,服裝可都很講究,窮的也有個窮講究——即使棉袍的面子是布的。也會設法安半截綢子里兒;即使連里子也得用布,還能在顏色上著想,襯上什么雪青的或深紫的。他們一律都卷著袖口,為是好顯顯小褂的潔白。 大概是因為忌妒吧,他們才說小陳是“兔子”;其實據我看呢,這群人們倒更象“那個”呢。 小陳一露面,他們的臉上就立刻擺出一種神情,能伸展成笑容,也能縮sa成怒意;一伸,就仿佛賞給了他一點世上罕有的恩寵;一縮,就好象他們觸犯帝王的圣怒。小陳,為博得彩聲,得向他們遞個求憐邀寵的眼色。連這么著,他們還不輕易給他喊個好兒。 趕到他們要捧的人上了台,他們的神情就極嚴肅了,都伸著脖兒聽;大家喊好的時候,他們不喊;他們卻在那大家不注意的地方,贊嘆著,仿佛是忘形的,不能不發泄的,喝一聲彩,使大家驚異,而且沒法不佩服他們是真懂行。據說,若是請他們吃一頓飯,他們便可以玩這一招。顯然的,小陳要打算減除了那種嘀咕,也得請他們吃飯。 我心里替小陳說,何必呢!可是他自有他的打算。五有一天,在報紙上,我看到小陳彩排的消息。我決定去看一看。 當然黑漢得給他預備下許多捧場的。我心里可有準兒,不能因為他得的好兒多或少去決定他的本事,我要憑著我自己的良心去判斷他的優劣。 他還是以作工討好,的確是好。至于唱工,憑良心說,連一個好兒也不值。在小屋里唱,不錯,他確是有味兒;一登台,他的嗓子未免太窄了,只有前兩排湊合著能聽見,稍微靠后一點的,便只見他張嘴而聽不見聲兒了。 想指著唱戲掙錢,談何容易呢!我曉得這個,可是不便去勸告他。黑漢會給他預備好捧場的,教他時時得到滿堂的彩,教他沒法不相信自己的技藝高明。我的話有什么用呢? 事后,報紙上的批評是一致的,都說他可以比作昔年的田桂鳳。我知道這些批評是由哪兒來的,黑漢哪能忘下這一招呢。 從這以后,義務戲和堂會就老有小陳的戲碼了。我沒有工夫去聽,可是心中替他擔憂。我曉得走票是花錢買臉的事,為玩票而傾家蕩產的并不算新奇;而小陳是個窮小子啊。打算露臉,他得有自己的行頭,得找好配角,得有跟包的,得擺出闊架子來,就憑他,公司里的一個小職員?難! 不錯,黑漢會幫助他;可是,一旦黑漢要翻臉和他算清賬怎么辦呢?俞先生的話,我現在明白過來,的確是經驗之談,一點也非過慮。 不久,我聽說他被公司辭了出來,原因是他私造了收據,使了一些錢。雖說我倆并非知己的朋友,我可深知他絕不是個小滑頭。要不是被逼急了,我相信他是不會干出這樣丟臉的事的。我原諒他,所以深恨黑漢和架弄著小陳的那一群人。 我決定去找他,看看我能不能幫助他一把兒;幾乎不為是幫助他,而是借此去反抗黑漢,要從黑漢手中把個聰明的青年救出來。 六 小陳的屋里有三四個人,都看著他作“活”呢。因為要省點錢,凡是自己能動手的,他便自己作。現在,他正作著一件背心,戲台上丫環所穿的那種。大家吸著煙,閑談著,他一聲不出的,正往背心上粘玻璃珠子——用膠水畫好一大枝梅花,而后把各色的玻璃珠粘上去,省工,省錢,而穿起來很明艷。 我進去,他只抬起頭來向我笑了笑,然后低下頭去繼續工作,仿佛是把我打入了那三四個人里邊去。我既不認識他們,又不想跟他們講話,只好呆呆的坐在那里。 那些人都年紀在四十以上,有的已留下胡子。聽他們所說的,看他們的神氣,我斷定他們都是一種票友。看他們的衣服,他們大概都是衙門里的小官兒,在家里和社會上也許是很熱心擁護舊禮教,而主張男女授受不親的。可是,他們來看小陳作活。他們都不野調無腔,談吐也頗文雅,只是他們的眼老溜著小陳,帶出一點于心不安而又無法克服的邪味的笑意。 他們談話兒,小陳并不大愛插嘴,可是趕到他們一提起某某伶人,或批評某某伶人的唱法,他便放下手中的活,皺起點眉來,極注意的聽著,而后神氣活似黑漢,斬釘截鐵的發表他的意見,話不多,可是十分的堅決,指出伶人們的缺點。他并不為自己吹騰,但是這種帶著堅固的自信的批判,已經足以顯出他自己的優越了。他已深信自己是獨一無二的旦角,除了他簡直沒有人懂戲。 好容易把他們耗走,我開始說我所要說的話,為省去繞彎,我開門見山的問了他一句:“你怎樣維持生活呢?” 他的臉忽然的紅了,大概是想起被公司辭退出來的那點恥辱。看他回不出話來,我爽性就釘到家吧:“你是不是已有許多的債?” 他勉強的笑了一下,可是神氣很堅決:“沒法不欠債。不過,那不算一回事,我會去掙。假如我現在有三千塊錢,作一批行頭,我馬上可以到上海去唱兩個星期,而后,”他的眼睛亮起來,“漢口,青島,濟南,天津,繞一個圈兒;回到這兒來,我就是——”他挑起大指頭。 “那么容易么?”我非常不客氣的問。 他看了我一眼,冷笑了一下,不屑于回答我。 “是你真相信你的本事,還是被債逼得沒法不走這條路呢?比如說,你現在已久下某人一兩千塊錢,去作個小事兒決不能還上,所以你想一下子去摟幾千來,而那個人也往這么引領你,是不是?” 想了一會兒,猶豫了一下,咽了一口氣,沒回答出什么來。我知道我的話是釘到他的心窩里。 “假若真象我剛才說的。”我往下說,“你該當想一想,現在你欠他的,那么你要是‘下海’,就還得向他借。他呢,就可以管轄你一輩子,不論你掙多少錢,也永遠還不清他的債,你的命就交給他了。捧起你來的人,也就是會要你命的人。你要是認為我不是嚇噱你,想法子還他的錢,我幫助你,找個事作,我幫助你,從此不再玩這一套。你想想看。” “為藝術是值得犧牲的!”他沒看我,說出這么一句。這回該我冷笑了。“是的,因為你在中學畢業,所以會說這么一句話,一句話,什么意思也沒有。” 他的臉又紅了。不愿再跟我說什么,因為越說他便越得氣餒;他的歲數不許他承認自己的錯誤。他向外邊喊了一聲:“二妹!你坐上一壺水!” 我這才曉得他還有個妹妹,我的心中可也就更不好過了;沒再說什么,我走了出去。 七 “全球馳名,第一青衫花旦陳……表演獨有歷史佳劇……”在報紙上,街頭上,都用極大的字登布出來。我知道小陳是“下了海”。 在“打炮”的兩天前,他在東海飯店招待新聞界和一些別的朋友。不知為什么,他也給了我張請帖。真不愿吃他這頓飯,可是我又要看看他,把請帖拿起又放下好幾回,最后我決定去看一眼。 席上一共有七八十人,有戲界的重要人物,有新聞記者,有捧角專家,有地面上的流氓。我沒大去注意這些人們,我仿佛是專為看小陳而來的。 他變了樣。衣服穿得頂講究,講究得使人看著難過,象新娘子打扮得那么不自然,那么過火。不過,這還不算出奇;最使人驚異的是右手的無名指上戴著個鉆石戒指,假若是真的,須值兩三千塊錢。誰送給他的呢?憑什么送給他呢?他的臉上分明的是擦了一點胭脂,還是那么削瘦,可是顯出點紅潤來。有這點假的血色在臉上,他的言語動作仿佛都是在作戲呢;他輕輕的扭轉脖子,好象唯恐損傷了那條高領子!他偏著臉向人說話,每說一句話先皺一下眉,而后嘴角用力的往上兜,故意的把腮上弄成兩個小坑兒。我看著他,我的脊背上一陣陣的起雞皮疙疸。 可是,我到底是原諒了他,因為黑漢在那里呢。黑漢是大都督,總管著一切:他拍大家的肩膀,向大家嘀咕,向小陳遞眼色,勸大家喝酒,隨著大家笑,出來進去,進去出來,用塊極大的綢子手絹擦著黑亮的腦門,手絹上抖出一股香水味。 據說,人熊見到人便過去拉住手狂笑。我沒看見過,可是我想象著那個樣子必定就象這個黑漢。 黑漢把我的眼睛引到一位五十來歲的矮胖子身上去。矮胖子坐首席,黑漢對他說的話最多,雖然矮胖子并不大愛回答,可是黑漢依然很恭敬。對了,我心中一亮,我找到那個鉆石戒指的來路! 再細看,我似乎認識那個胖臉。啊,想起來了,在報紙和雜志上見過:楚總長!楚總長是熱心提倡“藝術”的。 不錯,一定是他,因為他只喝了一杯酒,和一點湯,便離席了。黑漢和小陳都極恭敬的送出去。再回到席上,黑漢開始向大家說玩笑話了,仿佛是表示:貴人已走,大家可以隨便吧。 吃了一道菜,我也溜出去了。 八 楚總長出錢,黑漢辦事。小陳住著總長的別墅,有了自己的衣箱,鉆石戒指,汽車。他只是摸不著錢,一切都由黑漢經手。 只要有小陳的戲,楚總長便有個包廂,有時候帶著小陳的妹妹一同來:看完戲,便一同回到別墅,住下。小陳的妹妹長得可是真美。 楚總長得到個美人,黑漢落下了不少的錢,小陳得去唱戲,而且被人叫做“兔子”。 大局是這么定好了,無論是誰也無法把小陳從火坑里拉出來了。他得死在他們手里,俞先生一點也沒說錯。九事忙,我一年多沒聽過一次戲。小陳的戲碼還常在報紙上看到,他得意與否可無從知道。 有一次,我到天津辦一點事,晚上獨自在旅館里非常的無聊,便找來小報看看戲園的廣告。新到的一個什么“香”,當晚有戲。我連這個什么“香”是男是女也不曉得,反正是為解悶吧,就決定去看看。對于新起來的角色,我永遠不希望他得怎樣的好,以免看完了失望,弄一肚子蹩扭。 這個什么“香”果然不怎么高明,排場很闊氣,可是唱作都不夠味兒,唱到后半截兒,簡直有點支持不下去的樣子。 唱戲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呢,我不由的想起小陳來。正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了黑漢。他輕快的由台門閃出來,斜著身和打鼓的說了兩句話,又輕快的閃了進去。 哈!又是這小子!我心里說。哼,我同時想到了,大概他已把小陳吸干了,又來耍這個什么“香”了!該死的東西!由天津回來,我遇見了俞先生,談著談著便談到了小陳,俞先生的耳朵比我的靈通,剛一提起小陳,他便嘆了口氣:“完嘍!妹妹被那個什么總長給扔下不管了,姑娘不姑娘,太太不太太的在家里悶著。他呢,給那個黑小子掙夠了錢,黑小子撒手不再管他了,連行頭還讓黑小子拿去多一半。誰不知道唱戲能掙錢呢,可是事兒并不那么簡單容易。玩票,能被人吃光了;使黑杵,混不上粥喝;下海,誰的氣也得受著,能吃飽就算不離。我全曉得,早就勸過他,可是……”俞先生似乎還有好些個話,但是只搖了搖頭。 十 又過了差不多半年,我到濟南有點事。小陳正在那里唱呢,他掛頭牌,二牌三牌是須生和武生,角色不算很硬,可也還看得過去。這里,連由北平天橋大棚里約來的角兒還要成千論百的拿包銀,那么小陳——即使我們承認他一切的弱點——總比由天橋來的強著許多了。我決定去看他的戲,仿佛也多少含著點捧捧場的意思,誰教我是他的朋友呢。那晚上他貼的是獨有的“本兒戲”,九點鐘就上場,文武帶打,還贈送戲詞。我恰好有點事,到九點一刻才起身到戲園去,一路上我還怕太晚了點,買不到票。到九點半我到了戲園,里里外外全清鍋子冷灶,由老遠就聽到鑼鼓響,可就是看不見什么人。由賣票人的神氣我就看出來,不上座兒;因為他非常的和氣,一伸手就給了我張四排十一號——頂好的座位。 四排以后,我進去一看,全空著呢。兩廊稀棱棱的有些人,樓上左右的包廂全空著。一眼望過去,台上被水月電照得青虛虛的,四個打旗的失了魂似的立在左右,中間坐著個穿紅袍的小生,都象紙糊的。台下處處是空椅子,只在前面有一堆兒人,都象心中有點委屈似的。世上最難看的是半空的戲園子——既不象戲園,又不象任何事情,仿佛是一種夢景似的。 我坐下不大會兒,鑼鼓換了響聲,椅墊桌裙全換了南繡的,繡著小陳的名子。一陣鑼鼓敲過,換了小鑼,小陳扭了出來。沒有一聲碰頭好——人少,誰也不好意思喊。我真要落淚! 他瘦得已不成樣子。因為瘦,所以顯著身量高,就象一條打扮好的刀魚似的。 并不因為人少而敷衍,反之,他的瘦臉上帶出一些高傲,堅決的神氣;唱,念,作派,處處用力;越沒有人叫好,他越努力;就好象那宣傳宗教的那么熱烈,那么不怕困苦。每唱完一段,回過頭去喝水的工夫,我看見他嗽得很厲害,嗽一陣,揉一揉胸口,才轉過臉來。他的嗓音還是那么窄小,可是作工已臻化境,每一抬手邁步都有尺寸,都恰到好處;耍一個身段,他便向台下打一眼,仿佛是對觀眾說:這還不值個好兒嗎?沒人叫好,始終沒人喊一聲好! 我忽然象發了狂,用盡了力量給他喝了幾聲彩。他看見了我,向我微微一點頭。我一直坐到了台上吹了嗚嘟嘟,雖然并沒聽清楚戲中情節到底是怎回事;我心中很亂。散了戲,我跑到后台去,他還上著裝便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幾乎是一把骨頭。 “等我卸了裝,”他笑了一下,“咱們談一談!” 我等了好大半天,因為他真象個姑娘,事事都作得很慢很仔細,頭上的每一朵花,每一串小珠子,都極小心的往下摘,看著跟包的給收好。 我跟他到了三義棧,已是夜里一點半鐘。 一進屋,他連我也不顧得招待了,躺在床上,手哆嗦著,點上了煙燈。吸了兩大口,他緩了緩氣:“沒這個,我簡直活不了啦!” 我點了點頭。我想不起說什么。設若我要說話,我就要說對他有些用處的,可是就憑我這個平凡的人,怎能救得了他呢?只好聽著他說吧,我仿佛成了個傻子。 又吸了一大口煙,他輕輕的掰了個橘子,放在口中一瓣。“你幾兒個來的?” 我簡單的告訴了他關于我自己的事,說完,我問他:“怎樣?” 他笑了笑:“這里的人不懂戲!” “賠錢?” “當然!”他不象以前那樣愛紅臉了,話說得非常的自然,而且絕沒有一點后悔的意思。“再唱兩天吧,要還是不行,簡直得把戲箱留在這兒!” “那不就糟了?” “誰說不是!”他嗽咳了一陣,揉了揉胸口。“玩藝好也沒用,人家不聽,咱有什么法兒呢?” 我要說:你的嗓子太窄,你看事太容易!可是我沒說。說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嗓子無從改好,他的生活已入了轍,他已吸慣了煙,他已有了很重的肺病;我干嗎既幫不了他,還惹他難受呢? “在北平大概好一點?”我為是給他一點安慰。“也不十分好,班子多,地方錢緊,也不容易,哪里也不容易!”他揉著一點橘子皮,心中不耐煩,可是要勉強著鎮定。 “可是,反正我對得起老郎神,玩藝地道,別的……”是的,玩藝地道;不用說,他還是自居為第一的花旦。失敗,困苦,壓迫,無法擺脫,給他造成了一點自信,他只仗著這點自信活著呢。有這點自信欺騙著他自己,他什么也不怕,什么也可以一笑置之;妹(www.lz13.cn)妹被人家糟踐了,金錢被人家騙去,自己只剩下一把骨頭與很深的煙癮;對誰也無益,對自己只招來毀滅;可是他自信玩藝兒地道。“好吧,咱們北平見吧!”我告辭走出來。 “你不等聽聽我的全本《鳳儀亭》啦?后天就露!”他立在屋門口對我說。 我沒說出什么來。 回到北平不久,我在小報上看到小陳死去的消息。他至多也不過才二十四五歲吧。 老舍作品_老舍散文集 老舍:一筒炮台煙 老舍:“火”車分頁:123
郁達夫:馬纓花開的時候 約莫到了夜半,覺得怎么也睡不著覺,于起來小便之后,放下玻璃溺器,就順便走上了向南開著的窗口。把窗帷牽了一牽,低身鉆了進去,上半身就象是三明治里的火腿,被夾在玻璃與窗帷的中間。 窗外面是二十邊的還不十分大缺的下弦月夜,園里的樹梢上,隙地上,白色線樣的柏油步道上,都灑滿了銀粉似的月光,在和半透明的黑影互相掩映。周圍只是沉寂、清幽,正象是夢里的世界。首夏的節季,按理是應該有點熱了,但從毛絨睡衣的織縫眼里侵襲進來的室中空氣,尖淋淋還有些兒涼冷的春意。 這兒是法國天主教會所辦的慈善醫院的特等病房樓,當今天早晨進院來的時候,那個粗暴的青年法國醫生,糊糊涂涂的諦聽了一遍之后,一直到晚上,還沒有回話。只傍晚的時候,那位戴白帽子的牧母來了一次。問她這病究竟是什么病?她也只微笑搖著頭,說要問過主任醫生,才能知道。 而現在卻已經是深沉的午夜了,這些吃慈善飯的人,實在也太沒有良心,太不負責任,太沒有對眾生的同類愛。幸而這病,還是輕的,假若是重病呢?這么的一擱,擱起十幾個鐘頭,難道起死回生的耶穌奇跡,果真的還能在現代的二十世紀里再出來的么? 心里頭這樣在恨著急著,我以前額部抵住了涼陰陰的玻璃窗面,雙眼盡在向窗外花園內的朦朧月色,和暗淡花陰,作無心的觀賞。立了幾分鐘,怨了幾分鐘,在心里學著羅蘭夫人的那句名句,叫著哭著: “慈善呀慈善!在你這令名之下,真不知害死了多少無為的犧牲者,養肥了多少卑劣的圣賢人!” 直等怨恨到了極點的時候,忽而抬起頭來一看,在微明的遠處,在一堆樹影的高頭,金光一閃,突然間卻看出了一個金色的十字架來。 “啊嚇不對,圣母馬利亞在顯靈了!” 心里這樣一轉,自然而然地毛發也豎起了尖端。再仔細一望,那個金色十字架,還在月光里閃爍著,動也不動一動。注視了一會,我也有點怕起來了,就逃也似地將目光移向了別處。可是到了這逃避之所的一堆黑樹蔭中逗留得不久,在這黑沉沉的背景里,又突然顯出了許多上尖下闊的白茫茫同心兒一樣,比蠟燭稍短的不吉利的白色物體來。一朵兩朵,七朵八朵,一眼望去,雖不十分多,但也并不少,這大約總是開殘未謝的木蘭花罷,為想自己寬一寬自已的心,這樣以最善的方法解釋著這一種白色的幻影,我就把身體一縮,退回自己床上來了。 進院后第二天的午前十點多鐘,那位含著神秘的微笑的牧母又靜靜兒同游水似地來到了我的床邊。 “醫生說你害的是黃疸病,應該食淡才行。” 柔和地這樣的說著,她又伸出手來為我診脈。她以一只手捏住了我的臂,擎起另外一只手,在看她自己臂上的表。我一言不發,只是張大了眼在打量她的全身上下的奇異的線和色。 頭上是由七八根直線和斜色線疊成的一頂雪也似的麻紗白帽子,白影下就是一張肉色微紅的柔嫩得同米粉似的臉。因為是睡在那里的緣故,我所看得出來的,只是半張同《神曲》封面畫上,印在那里的譚戴似的鼻梁很高的側面形。而那只瞳人很大很黑的眼睛哩,卻又同在做夢似地向下斜俯著的。足以打破這沉沉的夢影,和靜靜的周圍的兩種刺激,便是她生在眼瞼上眼睛上的那些很長很黑,雖不十分粗,但卻也一根一根地明細分視得出來的眼睫毛和八字眉,與唧唧唧唧,只在她那只肥白的手臂上靜走的表針聲。她靜寂地俯著頭,按著我的臂,有時候也眨著眼睛,胸口頭很細很細的一低一高地吐著氣,真不知道聽了我幾多時的脈,忽而將身體一側,又微笑著正向著我顯示起全面來了,面形是一張中突而長圓的鵝蛋臉。 “你的脈并不快,大約養幾天,總馬上會好的。” 她的富有著抑揚風韻的話,卻是純粹的北京音。 “是會好的么?不會死的么?” “啐,您說哪兒的話?” 似乎是嫌我說得太粗暴了,嫣然地一笑,她就立刻靜肅敏捷地走轉了身,走出了房。而那個“啐,你說哪兒的話?”的余音,卻同大鐘鳴后,不肯立時靜息般的盡在我的腦里耳[口宏][口宏]地跑著繞圈兒的馬。 醫生隔日一來,而苦里帶咸的藥,一天卻要吞服四遍,但足與這些恨事相抵而有余的,倒是那牧母的靜肅的降臨,有幾天她來的次數,竟會比服藥的次數多一兩回。象這樣單調無聊的修道院似的病囚生活,不消說是誰也會感到厭膩的,我于住了一禮拜醫院之后,率性連醫生也不愿他來,藥也不想再服了,可是那牧母的診脈哩,我卻只希望她從早到晨起就來替我診視,一直到晚,不要離開。 起初她來的時候,只不過是含著微笑,量量熱度,診診我的脈,和說幾句不得不說的話而已。但后來有一天在我的枕頭底下被她搜出了一冊泥而宋版的Baudelaire的小冊子后,她和我說的話也多了起來,在我床邊逗留的時間也一次一次的長起來了。 她告訴了我Soeurs de charite(白帽子會)的系統和義務,她也告訴了我羅曼加多力克教(Catechisme)的教義總綱領。她說她的哥哥曾經去羅馬朝見過教皇,她說她的信心堅定是在十五年前的十四歲的時候。而她的所最對我表示同情的一點,似乎是因為我的老家的遠處在北京,“一個人單身病倒了在這舉目無親的上海,哪能夠不感到異樣的孤凄與寂寞呢?”尤其是覺得巧合的,兩人在談話的中間,竟發現了兩人的老家,都偏處在西城,相去不上二三百步路遠,在兩家的院子里,是都可以聽得見北堂的晨鐘暮鼓的。為有這種種的關系,我入院后經過了一禮拜的時候,覺得忌淡也沒有什么苦處了,因為每次的膳事,她總叫廚子特別的為我留心,布丁上的奶油也特別的加得多,有幾次并且為了醫院內的定食不合我的胃口,她竟愛把她自己的幾盆我可以吃的菜蔬,差男護士菲列浦一盆一盆的遞送過來,來和我的交換。 象這樣的在病院里住了半個多月,雖則醫生的粗暴頑迷,仍舊改不過來,藥味的酸咸帶苦,仍舊是格格難吃,但小便中的絳黃色,卻也漸漸地褪去,而柔軟無力的兩只腳,也能夠走得動一里以上的路了。 又加以時節逼進中夏,日長的午后,火熱的太陽偏西一點,在房間里悶坐不住,當晚禱之前,她也常肯來和我向樓下的花園里去散一回小步。兩人從庭前走出,沿了葡萄架的甬道走過木蘭花叢,穿入菩提樹林,到前面的假山石旁,有金色十字架豎著的圣母像的石壇圈里,總要在長椅上,坐到晚禱的時候,才走回來。 這舒徐閑適的半小時的晚步,起初不過是隔兩日一次或隔日一次的,后來竟成了習慣,變得日日非去走不行了。這在我當然是一種無上的慰藉,可以打破一整天的單調生活,而終日忙碌的她似乎也在對這漫步,感受著無窮的興趣。 又經過了一星期的光景,天氣更加熱起來了。園里的各種花木,都已經開落得干干凈凈,只有墻角上的一叢灌木,大約是薔薇罷,還剩著幾朵紅白的殘花,在那里妝點著景色。去盛夏想也已不遠,而我也在打算退出這醫藥費昂貴的慈善醫院,轉回到北京去過夏去。可是心里雖則在這么的打算,但一則究竟病還沒有痊愈,而二則對于這周圍的花木,對于這半月余的生活情趣,也覺得有點依依難舍,所以一天一天的捱捱,又過了幾天無聊的病囚日子。 有一天午后,正當前兩天的大雨之余,天氣爽朗晴和得特別可愛,我在病室里踱來踱去,心里頭感覺得異樣的焦悶。大約在鐵籠子里徘徊著的新被擒獲的獅子,或可以想象得出我此時的心境來,因為那一天從早晨起,一直到將近晚禱的時候止,一整日中,牧母還不曾來過。 晚步的時間過去了,電燈點上了,直到送晚餐來的時候,菲列浦才從他的那件白衣袋里,摸出了一封信來,這不消說是牧母托他轉交的信。 信里說,她今天上中央會堂去避靜去了,休息些時,她將要離開上海,被調到香港的病院中去服務。若來面別,難免得不動傷感,所以相見不如不見。末后再三叮囑著,教我好好的保養,靜想想經傳上圣人的生活。若我能因這次的染病,而歸依上帝,浴圣母的慈恩,那她的喜悅就沒有比此更大的了。 我讀了這一封信后,夜飯當然是一瓢也沒有下咽。在電燈下呆坐了數十分鐘,站將起來向窗外面一看,明藍的天空里,卻早已經升上了一個銀盆似的月亮。大約不是十五六,也該是十三四的晚上了。 我在窗前又呆立了一會,旋轉身就披上了一件新制的法蘭絨的長衫,拿起了手杖,慢慢地,慢慢地,走下了樓梯,走出了樓門,走上了那條我們兩人日日在晚禱時候走熟了的葡萄甬道。一程一程的走去,月光就在我的身上印出了許多樹枝和疊石的影畫。到了那圣母像的石壇之內,我在那張兩人坐熟了的長椅子上,不知獨坐了多少時候。忽而來了一陣微風,我偶然間卻聞著了一種極清幽,極淡漠的似花又似葉的朦朧的香氣。稍稍移了一移擱在支著手杖的兩只手背上的頭部,向右肩瞟了一眼,在我自己的衣服上,卻又看出了一排非常纖勻的對稱樹葉的葉影,和幾朵花蕊細長花瓣稀薄的花影來。 “啊啊!馬纓花開了!” 毫不自覺的從嘴里輕輕念出了這一(www.lz13.cn)句獨語之后,我就從長椅子上站起了身來,走回了病舍。 一九三二年六月 原載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現代》第一卷第四期 郁達夫作品_郁達夫散文集 郁達夫散文讀后感 郁達夫詩詞分頁:123
林清玄:讓開心成為一種習慣 一、快樂活在當下,盡心就是完美 很小很小的時候,我就感覺到花是非常奇怪的,因為在家院的庭前種了桂花、玉蘭和夜來香,到了晚上,香氣隨同四散,流動在家屋四周,可是這些香花都是白色的。反而那些極美麗的花卉,像蘭花、玫瑰之屬,就沒有什么香味了。 長大以后,才更發現這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凡香氣極盛的花,桂花、玉蘭花、夜來香、含笑花、水姜花、月桃花、百合花、梔子花、七里香,都是白色,即使有顏色也是非常素淡,而且它們開放的時候常成群結隊的,熱鬧紛繁。那些顏色艷麗的花,則都是孤芳自賞,每一枝只開出一朵,也吝惜著香氣一般,很少有香味的。 “香花無色,色花不香”這真是一個驚人的發現;“素樸的花喜歡成群結隊,美艷的花喜歡幽然獨處”也是驚人的發現。依照植物學家的說法,白花為了吸引蜂蝶傳播花粉,因此放散濃厚的芳香;美麗的花則不必如此,只要以它的顏色就能招蜂引蝶了。我們不管植物學家的說法,就單以“香花無色,色花不香”就可以給我們許多聯想,并帶來人生的啟示。 在人生里,每一個人都有其獨特非凡的素質,有的香盛,有的色濃,很少很少能兼具美麗而芳香的,因此我們不必欣羨別人某些天生的的素質,而要發現自我獨特的風格。當然,我們的人生多少都有缺憾,這缺憾的哲學其實簡單:連最名貴的蘭花,恐怕都為自己不能芳香而落淚哩!這是對待自己的方法,也是面對自己缺憾還能自在的方法。 面對外在世界的時候,我們不要被艷麗的顏色所迷惑,而要進入事物的實相,有許多東西表面是非常平凡的,它的顏色也素樸,但只要我們讓心平靜下來,就能品察出這內部最幽深的芳香。 當然,艷麗之美有時也值得贊嘆,只是它適于遠觀,不適于沉潛。 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很少能欣賞素樸的事物,卻喜歡耀目的風華;但到了中年則愈來愈喜歡那些真實平凡的素質,例如選用一張桌子,青年多會注意到它的顏色與造形之美,中年人就比較注意它是紫檀木或是烏心石的材質,至于外形與色彩就在其次了。 最近這些日子里,我時常有一種新的感懷,就是和一個人面對面說了許多話,仿佛一句話也沒有說;可是和另一個人面對面坐著,什么話也沒有說,就仿佛說了很多。人到了某一個年紀、某一個階段,就能穿破語言、表情、動作,直接以心來相印了,也就是用素樸面對著素樸。 古印度人說,人應該把中年以后的歲月全部用來自覺和思索,以便找尋自我最深處的芳香。我們可能做不到那樣,不過,假如一個人到了中年,還不能從心靈自然地散出芬芳,那就象白色的玉蘭或含笑,竟然沒有任何香氣,一樣的可悲了。 二、讓開心成為一種習慣 已看慣了太陽的東升西落,月亮的陰晴圓缺;習慣了春夏秋冬的冷暖,世間萬物的改變;卻很難看淡人間的悲歡離合、情仇恩怨,更難將傷心難過看得風清云淡。經過了很多年的改變以后,將開心當成了一種習慣,于是我發現我的開心感染了很多人,人們問我為什么的時候,我只說:開心是一種習慣! 以前常常討厭世人那些所謂的好心忠告,因為明明知道沒有幾個人能做得到,事事喜歡去斤斤計較,到頭來傷心難過的只是自已。常常聽不習慣朋友的花言巧語,看不習慣朋友的惺惺假意,突然恨透了這個世界,感覺到處都是虛偽的面孔。 也許是因為經歷的太多,也許是因為個人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社會的情況下只能順應了這個社會,于是喜歡上西門子公司的一句企業文化:“請愉快地工作。”并改成了“請開心地生活。”的確,開心與不開心,都要過一天24個小時,何不開心的渡過每一天呢? 當然,沒有哪個人在面對傷心和難過的時候還可以傻笑,但是,你卻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去調整自己的心態。(www.lz13.cn)要知道傷心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于是,我將那句話刻在了心里:“請開心地生活。”這樣時時刻刻提醒自已,我應該開心的過每一天,因為我像所有人一樣,希望自已能過的好一點,雖然不能從物質上滿足自已,但是已學會彌補自已心靈上的空虛。 人的一生,總有學不完的知識,總有領悟不透的真理,總有一些有意或者無意的煩心事闖到心里來,總之,生之夢,順少逆多,一輩子不容易,千萬不要總是跟別人過不去,更不要跟自已過不去。書上云:看別人不順眼是自已的修養不夠。想一下也是,因為每個人的出身背景、受教育程度、受社會影響都是不一樣的,在你看不慣別人的同時,是否別人也看不慣你呢?所以開心的去面對每一個人,要學會看朋友身上的優點,學習朋友身上的優點,朋友的缺點正是你最好的反面教材,如果你也有這樣的缺點請及時改善,不正是你所期望的嗎? 開心不僅僅是心里的感覺,而是因為你有了開心的感覺,于是別人可以從你的臉上讀到微笑,讀到開心。如果你在生活中比較細心的話,你就會知道世間最美麗的表情就是微笑,如果你天天想擁用世間最美麗的表情,那么請把開心當成一種習慣吧! 心隨境轉是凡夫,境隨心轉是圣賢。 用慚愧心看自己,用感恩心看世界。 林清玄:你應該掌握的六種能力 林清玄經典語錄 林清玄散文讀后感分頁:123
ACC711CEV55C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